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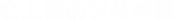
去下载 APP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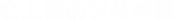

然而毫无疑问,栀子花的确是有种颠覆人感官的香,这种香,吃栀子以外,我只有一次体会过,就是“天麻刺身”,其实就是根据日本人吃鲜鱼片的原理,把新鲜的肉质肥厚的上等天麻切成极薄的片,为数不多的几片薄如蝉翼的天麻,放在一大盘冰上,佐以老北京地道的芝麻和辣椒酱,那鲜香,也是无与伦比。
但天麻刺身的鲜香跟栀子的馥郁香有差异,后者的香味,甚至使我在长达二十几年的光阴里,都固执地怀念曾经在乡下生活的那些日子,那种有洁净水、有自由空气、还有浩荡蓝天的生活,每天吃不完的栀子花、覆盆子、杨梅、腌木瓜。那时,爷爷为了给我解馋,会乐此不疲地发明各种吃食,比如有一种冰凉粉,就是用红糖水、薄荷和一点点醋制成的,是整个童年最难忘的消暑美食。
眼下又是栀子季,昨晚去花市,挤挤嚷嚷的花卉市场里,最多的就是栀子,还有猪笼草。猪笼草形状虽恐怖,但它其实不失为一个极好的爱情隐喻,诱惑、捕杀、再消化,一切迅疾无声。至于那些不管不顾香着的栀子,开败了的都贱卖,尚未绽开花苞的都特贵。
节选自《万物赠我浓情蜜意》

 打开形色,查看全部评论
打开形色,查看全部评论